

文/羊城派记者 董柳
广州市民刘某强闯妻子出租屋抓奸找证据,却被法院以非法侵入住宅罪判刑六个月。
在夫妻感情破裂而分居期间,夫妻一方前往另一方的出租屋偷拍偷录,这样取得的证据算数吗?雇佣私家侦探取得的证据是合法证据吗?怎样“陷阱取证”才能获法院认可?
在广州市律师协会、广东蒿芃燊晟律师事务所等近日联合举办的HOPE法律讲坛上,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证据法法学家、博士生导师廖中洪讲述了“民事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据他介绍,偷拍偷录是目前民事诉讼证据领域中越来越突出的一个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违背公序良俗的取证属非法证据
“我们所说的非法证据,实质上就是缺乏合法性的证据。换言之,证据本身有可能是真实的,但是由于它侵害了法律所保护的其他利益,而成为了法律所禁止的证据。”廖中洪说。
2015年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6条规定:“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他举例说,几年前,四川有一个老板想离婚,又不想分财产给前妻,于是找了个男青年去勾引自己老婆,承诺事前给3万,事后给2万。
该男青年按约定去做了,发微信、打电话,两人还去开房,并被事先安排好的摄像机偷偷录了下来。但该老板并未兑现承诺,最后的2万元未支付,于是在法院审理离婚案过程中,该男青年把事情经过讲了出来。
廖中洪表示,该案中女方出轨是事实,但该老板让人引诱并偷拍取证行为违反了公序良俗,最后法院认定其出轨证据属于非法证据。
专业窃听器材取证也属非法证据
廖中洪说,非法证据排除的衡量标准,一要看器材。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窃听、窃照专用器材而取得的视听资料属非法证据。对这些器材,国家工商总局、公安部、国家质监总局颁布的《禁止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和“伪基站”设备的规定》有明确规定。
常见的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包括微型针孔式摄像装置以及使用微型针孔式摄像装置的照相、摄像器材等。
二要看使用的场所。根据公共场所无隐私的原则,在公共场所偷拍的视听资料原则上属于合法证据。而在私密场所偷拍证据的合法性非常复杂,一般应根据当事人是否对该场具有支配权来确定。
例如,夫妻之间所涉及的偷拍证据就要分具体情况:
一种是对其所共同住所拥有支配权的情形,如一方带情人回家被配偶偷拍,则该证据没有侵犯隐私,属合法证据,因为双方对自己的家都有支配权;
二是在夫妻感情破裂而分居期间,夫妻一方前往另一方的出租屋偷拍取证,这种情况比较有争议。2015年广州市越秀区法院就丈夫强闯妻子的出租屋抓奸打人一案作出了刑事判决,以非法侵入住宅罪对该男子判刑。
从该案可以看出,夫妻感情破裂而分居期间,双方对自己的住所有独立排他的支配权,未经许可进行拍摄也会侵犯隐私。
雇请私家侦探取得的证据合法吗?
廖中洪介绍,重庆有个案子争议较大,两夫妻40多岁,两个是不同公司的高管,女方发现丈夫不对劲,就找高手把丈夫的电脑打开了,把丈夫出轨的电子资料全部拷贝下来,拿到了法院上作为证据。
法院也表示为难,并有多种不同观点。廖中洪说,首先婚姻法规定,婚姻存续期间的财产是夫妻共有的,这个电脑是否属于共有财产?其次,婚姻期间也是有个人隐私的,女方这么做算不算侵犯隐私权?
“我的个人观点保守一点”,廖中洪表示,他认为不存在侵害他人权益,女方这样取得的证据不属于非法证据。
如何对私人侦探所收集的证据进行合法性判断?
廖中洪分析,若其行为侵害了有关人的合法权益或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则该特定证据便属于违法收集的证据应受排除,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反之,若私人侦探收集证据的行为本身是合法的,则不因其收集主体为私人侦探而受到排除,即仅凭取证主体身份不足以否定证据的效力。
偷拍偷录得到的视听资料算数吗?
“偷拍偷录是目前民事诉讼证据领域中越来越突出的一个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其复杂性不仅表现在法律规定不具体,主要的还在于具体情况十分复杂。”廖中洪说。
他介绍,从偷拍偷录行为的主体看,有当事人本人即原告,有原告的直系亲属,有原告委托的一般人,也有专门从事民间偷拍偷录的私人侦探公司;
从偷拍偷录行为发生的地点看,有公共场所,也有私人领域;从涉及的人员而言,有的只涉及当事人之间,有的涉及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员的利益与权利;
从使用的方法看,有的使用了威胁性语言,有的没有;
从偷拍偷录使用的工具看,有的使用的是法律禁止的工具,针孔摄像机、电话窃听器等,也的是一般日常生活工具,如手机等。
同时,这些因素还存在交叉。如虽是在自己家里,但使用的是针孔摄像机等,为此,哪些情况下属于违法获取的证据,以及那些不属于,往往难于分辨,需在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6条的基础上,视具体案件分析。
怎样“陷阱取证”才能获法院认可?
廖中洪介绍,民事诉讼中的陷阱取证,分为犯意诱发型和机会提供型两种。“目前,世界各国都普遍承认机会提供型陷阱取证的正当性,而否定犯意诱发型陷阱取证的正当性。原因在于,侵权必须是在自由意志支配下实施的行为,如果是在他人引诱下实施,那么应该追究的是实施引诱行为者的责任,而不是侵权行为人。”
他说,“陷阱取证”的最大问题是进行取证的过程中,当事人或公证人员通常需要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整个过程的目的也是为了获取证据,所以有一定的欺骗性。为此,对于这种取证方式所取得证据的性质存在争议。
在一宗著名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中,北京几家公司通过利诱方式获取了有关另几家公司侵权的证据,北京一中院认可了“陷阱取证”,北京高院终审判决认为原告采取“陷阱取证”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最高法院再审又认可了“陷阱取证”。
为何同案不同判?廖中洪说,衡量民事陷阱取证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首先,要把握原则。当事人取证时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也没有严重危害公共利益,那么法院不应该排除通过此种手段取得的证据。
其次,民事陷阱取证的适用对象应当限于特定类型的案件中,主要是针对有较强隐蔽性的侵权案件,且只能对当事人有初步证据证明有侵权倾向并准备实施或已实施侵权行为。
再次,强化民事陷阱取证的程序保障。当事人可向公证机关申请对陷阱取证的方式进行公证,公证可以证明并确保当事人的取证过程合法有效。(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来源|羊城派
责编|郑宗敏
图片|视觉中国(图文无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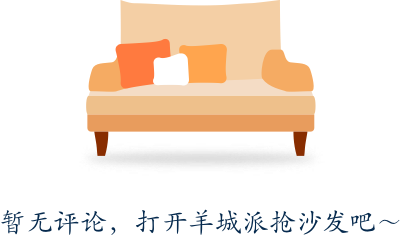
请点击右上角的「 ••• 」按钮
选择「在浏览器中打开」
未安装羊城派App?
遇到无法打开网页吗?
请点击下面按钮
未安装羊城派App?
请点击右上角的「 ••• 」按钮
选择「分享到朋友圈」或其他分享方式~
最新评论